首页 → 新闻频道 → 人物访谈  |
|
|
乔全生:让易道十年间华丽转身
日期:2008-09-11 来源:《风景园林》2008年第二期 作者:文桦 我要评论()
有人说易道的东西缺乏一致风格,或者说缺乏一致风格就是易道的风格,我觉得这话讲得不够到位。我们更多地是针对项目环境背景来进行创作,针对一个没有时间性的东西来做设计,我们希望的开放空间是一个简洁的背景,一个让人来使用的空间和一个没有时间限制性的设计。 乔全生:1997年,易道开始接触这个项目,到目前,跨度长达十年。原来的总体规划并非我们的作品,但我们理解到那个总体规划存在很多问题。最初业主提出让我们在三个月内把环湖将近六公里水面、沿湖宽100米的陆地绿化起来。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机会,有希望建成一个国际水平的新地标,创造一个一流的城市滨水空间。这个滨水空间必须要处理好人、城市和水岸的关系。同时借助这个滨水空间来定义这个城市在不同段落所应该出现的不同表情、质感和土地使用方式,提升周边土地的价值,创造城市的风格和形象。因此,它的任务很多重。我们当时提出了许多新概念,但在那个时候推动起来很困难。业主最初并没把我们的设计照单全收,因为这与他们对水岸的理解完全不一样。按以往的做法,在开放空间里不应该安排有商业活动,所有的开放空间都应该在划好的红线内,建筑不应该推到水边。其他包括设计语言、施工材料和施工方法,都面临着非常大的考验。在工作过程中,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做样板段、再修改样板。期间,我们也有过怀疑,但没有放弃,坚持实现最初的理想。 伯乐识良驹。设计方与业主彼此之间的支持、理解,甚至妥协,对于创造一个好的作品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正是因为甲方、乙方以及施工方互相配合默契,对项目品质有共同追求,才使这个项目得以成功。尽管我们现在已经逐渐退出金鸡湖的后续建设,但十年来,当初我们做的那些段落一直为人津津乐道,我觉得还是非常安慰的。 乔全生:海河因为原有航运的没落而没落了,成为了城市中一个防洪排涝的水体。然而,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对于河流空间的憧憬和想法从未中断。我们介入的段落是从天津三岔口京杭大运河的交接口到天津外环线,近18公里长的沿线景观总体规划。2002年,我们花了近10个月才完成了项目的景观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之后,开始第一期长约4.5公里河岸两边景观建设,2004年完工。
在过去中国十几二十年的城市发展中,我们不断在构筑标志性的建筑物,如东方明珠、CCTV新大楼、鸟巢等,但这些建筑不能当作城市现代文明的象征。我们的城市不仅仅需要一些点,更需要由点连成线、由线连成面;不仅仅要景观,更要实质的空间品质,或者是一种环境的意境。 另外,我们一直强调大家不应该把景观单纯看作是绿化。城市建设是个复合体,过去我们很重视建筑本身和绿化。但绿化有的时候是一个表象的东西,目的是让城市看起来比较美丽。这种表象的美丽有时会带来很多问题。我们更希望大家能把城市当成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来处理,包括建筑、景观、交通、市政、生态、经济、文化等等。当我们这么来看待城市时,我们就会反省过去的一些简单化做法。 乔全生:“境筑”的确不是景观公司单独能承担的,也绝对不是易道一家公司能完成的。它的实现需要多个部门的合作。关键在观念,领导在要求构筑标志性建筑的同时,更应强调开放空间的延续性、公交系统的便捷和舒适性、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等问题。所以,我在多种场合借领导和学校的耳朵,不断地呼吁,希望给予这些问题更多关注。在这件事情上,我不敢说我们是一个革命家,但可以说我们是一个鼓吹者,扮演着一个先锋角色。 乔全生:“境筑”其实给业主提供了更多的思考层面。我们给业主推荐这种方法时,不少业主能理解,也愿意尝试。像我们刚刚完成的深圳东部滨海地区项目,还有马上要进行的重庆两江四岸规划和天津生态城,都是以复合的态度,从生态、经济、文化等多角度来处理。当然,并不是每个项目都需要这样的工作方法。当面对城市周边的新区建设这类项目时,给业主提供的城市规划框架会更长远,思索的内容会更复杂。 乔全生:批评对项目其实是很重要的,易道公司内部就建立了自我批评机制。但我需要指出,设计师一定要有自己的理想,别人怎么批评你的东西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过好自己这一关,要坚持自己的设计方向、原则和态度。 坦白讲,易道在中国并不是每一个作品都是经典之作,我们也会有一些失败的作品,那些项目可能是当时设计师经验不足,或者是跟业主沟通不好等原因造成的。这些批评我们都虚心接受。但如果只是为了迎合社会而设计出一些没有自我要求的东西,这对于设计师来说更为可悲。 乔全生:用“文化大棒”来敲打,我们首先应当虚心接受,但有时候也觉得冤枉。易道的目标是做一个本土化的国际公司。必须谦虚地讲,我们可能还做得不够深、不够好,但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认为本土化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人的本土化,现在易道在中国分支机构中有70%是国内人员。他们中有的大学一毕业就在易道,有的从国外留学后来到易道,在易道的培养下不断成长。他们了解本土知识,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其次,我们跟国内的甲方、学术机构以及政府部门一直在不断地建立专业上的关系,勤勤恳恳地向前推进。 在项目设计上,相对来说,国内对文化表达的要求大多还停留在比较皮相的东西上,比如说符号。当然不是说我们已经有了完美的答案,但我觉得文化在可持续发展层面也是十分重要,怎样活出现代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的精神文明,不是仅仅用符号就能诠释的。牵强附会地使用符号,不仅令人心痛,而且具有很强的讽刺性。 行事温润如玉,却暗含锋芒;言词含蓄婉转,却不避时弊。“揉碎了之后的重组”是乔全生对自己的评价。 大学建筑系的第一节设计课上,老师布置同学们去校园附近的小区体验,并做出建筑方案,可以是餐厅,也可以是住宅。回来后,全班的同学都忙着按老师的要求“盖房子”,唯有一个学生,他独对小区中间的三角形空地产生了很大兴趣,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个公共空间。这个特立独行的学生就是乔全生。 “吸引我的是,公园在这里可以形成一个精彩的开放空间,让小区的人们在这个公共空间里发生很多故事。” “我对设计的激情从来不仅在单体的建筑,而是整体的环境。” “为什么不同区域的街道,它两边的商店会有着不同的风格?谁创造了这样的空间?谁使用这样的空间?为什么这些空间能使这个城市富有了生命力?这些都是念书时,最让我感兴趣、感动的东西。” 带着这些兴趣和感动,1985年乔全生只身来到美国西岸,开始了自己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设计学院建筑系的学习生活。 “第一年非常痛苦。因为我从小在台湾长大,父母都是高校教员,我又是家中长子,家教非常严格、传统。那时候,在我看来,什么是黑,什么是白,都清清楚楚,不容置疑,这些正是从社会、学校和家庭中得到的教育和价值观。而到了美国以后才发现,从前所认为的“黑”并不一定黑,“白”也不一定就是白,这个世界还可以通过其他视角去看、去理解。这使得我原先建立起来的所有的价值观都要摧毁重来。” “人家给过你,你自己又重新整理过一次,这有好处。你会有很强的自信,你知道什么是自己的。这个过程对我影响最大。” 乔全生觉得自己的运气很好,因为伯克利是一所非常开放、完全自由的学校,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地去尝试新鲜事物。而伯克利不仅拥有全美最出色的图书馆系统,其环境设计学院也颇具专业名望。顺利地拿到建筑学硕士学位后,乔全生又被父亲“逼着”上了哈佛大学。在这所以学风严谨闻名于世的学校里,乔全生选择了城市设计专业,他对城市空间的思考在这里得到了更为扎实的梳理和深化。 “如果我只去了伯克利,没有去哈佛,或者只去了哈佛,没有去伯克利,可能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一个软,一个硬;一个热,一个冷,造就了我现在这种刚柔并济的做事风格。” 1988年,乔全生完成学业,获得哈佛大学城市设计硕士学位,开始了自己的专业历程。从此,这位经历了中西价值观洗礼,又被截然不同教育风格打造出来的青年,浸染于城市空间的玄妙世界里,一干已是20年。 乔全生:有啊!我毕业后四年左右,在美国西岸一位城市设计大师手下工作。有一回,我连续加班熬夜好几天,终于把设计方案做好了,然后回去休息。第二天,大师来得很早,但他完全不顾我几天以来的辛苦,把桌上的图全部改掉了。当时,我真有一种被彻底否定的感觉。所以,现在我对待员工,如果他们有的设计做得不好,我会尽量友善地指出来,而不是直接“摧毁”他们的信心。(开心地大笑) 像这样的挫折,我把它看成是历练自己的机会。任何一个健康向上的人,都会去思考,然后通过自省、与别人的沟通,慢慢地提升自己。现在我在公司内部也是这样要求,如果员工需要沟通,他们可以随时来找我。你可能表达的内容不一定正确,但一定要珍惜表达的机会,易道的管理是追求水平横向而不是垂直纵向的。 乔全生:作为易道亚洲区的主席,我的主要任务是在未来的五年内,把易道亚洲的业务从目前70%在国内真正做到一半在中国内,一半在中国之外。开拓中国以外的东南亚和印度和中东的市场,由于东南亚有许多不同的文化,面临的问题可能要更复杂些。我相信,我们在中国十年累积的经验和许多非常优秀的专业人才会让我们在东南亚、印度和中东的发展走得更轻松一些。另外,美国易道在全球已经设有28个分支机构,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和规范的硬件配置做保证,比方说,我们的员工可以今天在旧金山工作,明天在北京办公室,工作环境没有太大差别。 乔全生:我还是说,要做最好的项目,要对我们的社会环境和生存环境带来最好的影响,产生最好的改变。这是我个人和易道公司的真诚抱负。只有我们自己做到最好,我们才能承接最好的项目,拿出最好的作品。
中国风景园林网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音频、视频)特供中国风景园林网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 热点推荐
企业服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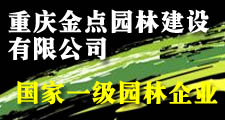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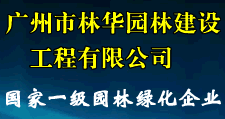
 包满珠:甘肃
包满珠:甘肃 EDSA总裁李建
EDSA总裁李建